
曾三(1906~1990),原名曾海云,益阳县(今赫山区)新市渡镇高冲村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和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先驱,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他是红军时期的无线电通信先驱,是红军第一批经过正规学校培养的无线电发报人员。后转战档案保密工作,是我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档案事业、档案工作、档案学理论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生于伟大时代,分担天下兴亡”是他一生的写照,父亲对他的教育,自己的身体力行,以及对后代子女的教育都浓于这一句话里。
父亲鞭罚下的教诲
1920年,曾三在益阳县立第二高小(即箴言书院)求学时因学校收取了学生取暖费而不给烤火,带领全班同学罢课。当时学校决定开除曾三等带头闹事的学生,通知发到家里后,父亲曾月卿并没有责备儿子,而是让儿子回学校,并说:“海云,学校来通知让我送你回去,有我陪着,不会有事的。你力气小,行李我担着,你跟着走就行。”曾三在后面看着父亲的背影,一路跟着到了学校。
等到了学校,面对校长和训教主任的高声喝问和指责,曾月卿低头连连称是。最后训教主任问到:“你儿子该不该罚?”曾月卿回答:“该罚。”又问道:“该不该打?”曾月卿回答到:“该打。”接着又说到:“子不教,父之过,海云今天这样,与我这个做父亲的分不开关系。”训教主任抓过桌子上的皮鞭往地上一扔,说到:“你自己动手吧。”曾月卿拿过皮鞭,俯身到儿子耳边说到:“海云,你忍着点。”二十鞭子,一下是一下,父亲抽得分明,儿子也不曾吭过半声。事后,曾月卿对儿子说到:“眼下读书是第一要事,现在国家如此局面,只有读书才能为国多出力,你不能没有书读,海云,你能明白?”曾三含着眼泪点了点头,曾月卿也含着一把老泪抱住了儿子。从此之后,曾三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工作当中都特别的发奋努力,因为父亲的话一直都深深地影响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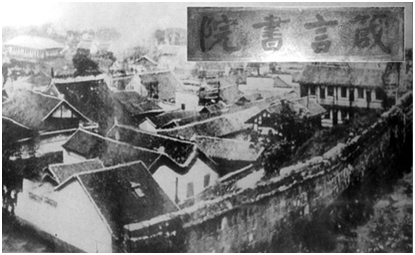
(箴言书院旧址)
生活实苦,不负明天
1930年,曾三在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当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为了安全起见,学员们都分散居住,曾三和伍云甫租住在一对夫妇家。培训班学习条件比较艰苦,设备也很简陋。学习用具只有一个电键、一个蜂鸣器、一块干电池,再加上几个拍纸簿和两支铅笔。上海的夏天是非常炎热的,曾三就打着赤膊练习,浑身都湿淋淋的。而曾三天天在房间里“滴滴嗒”“嗒嗒滴” ,这自然引起了房东的怀疑。一次房东问到:“天气这么热,你整天在房间里滴滴答答的,不出去凉快凉快,这是干什么呀?”曾三回答到:“学无线电,上海找工作不容易,要赶紧学一门技术好找工作,也就顾不得热了。”“你们在哪个学校学习呀?”房东又问。“我们没上学,只请了一个朋友来教,每月给他一些钱。”当时,这种情况在上海比较普遍,所以房东也没有再多问。

然而生活上的困难并不轻于学习上的困难。由于经费拮据,曾三等人的生活经费经常不能保障,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本不算什么。可是在纸醉金迷的上海,生活过得太寒酸不仅会被看成“瘪三”,更会引起其他方面的怀疑。在学习期间,组织上给他们每人每月七、八元钱的生活费,除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用在伙食上的钱就不多了,每天基本上就是一把小菜、一块酱豆腐,偶尔会买几角钱的肉放在案板上故意给房东看到。
端午节那天,没有米下锅了,快到中午,房东见曾三等人还没有生火做饭,不知是出于无心还是有意,问到:“今天过节,弄什么好吃的呀?”这一问把曾三他们问愣了。怎么说呢?如实讲肯定不行,这时一起学习的伍云甫回答到:“今天不做饭,有朋友约我们到他家里过节。”曾三也接着到:“对,快到时候了,我们该动身了吧?”就这样曾三他们不得不出门装装样子。
这段在上海学习无线电的日子是曾三一生最为难忘的几段时光之一,在这里他克服了诸多困难,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但最难克服的还是对家乡和亲人们的思念。而那个时候就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能尽早将党的无线电事业建立起来。
身陷囹圄,不忘初心
“文革”爆发后,“四人帮”诬陷杨尚昆、曾三“盗窃党的核心档案机密”,曾三随即被打倒,撤销了他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等一切职务。1969年曾三被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劳动改造,期间饱受折磨,每天就是劳动——批斗,批斗——劳动,这使得曾三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总有一天会弄清真相,给予平反。然而更令曾三揪心的是,“文革”初始,全国各地就有大批档案馆受到冲击,国家机密遭到疯狂破坏,损失异常惨重。化工部被抢走机密档案资料多达11卡车;中央统战部机关档案被一抢而光;交通部党组档案被抢走翻阅、抄写、张贴,致使党和国家机密泄露;更胆寒的是在当时最为机密的导弹资料都被人抢夺,最后是周总理亲自过问才拦下这批档案资料。听到这些消息的曾三跺着脚喊道:“这是犯罪啊!也对不起子孙后代啊!”他越想越心碎,但是却无能为力,只能想着出去以后要怎样来拯救破坏殆尽的档案事业。
“文革”结束后,曾三马上向中央提出要为档案工作平反,恢复国家档案局、恢复中央档案馆,得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坚决支持,曾三的职务也得到恢复,问题解决后他便迫不及待的投入到了档案事业的恢复工作当中。
子孙后代,各凭本事
曾三一共有六个儿女,他对子女的教育特别注重细节,他要求子女们站要有站样,坐要有坐样,用筷子手指头是绝对不能翘起来的,吃饭不能在盘子里去挑,看好了夹过来就得吃。就是这种注重细节的教育,使得曾三的几
个儿女都养成了很好的品行,生活中兄弟姐妹相互关照,做起事来严谨有序。
曾三对家人的要求十分严格。当时任益阳地委书记的何晓明询问曾三的侄儿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他听闻后直接从北京挂电话到益阳拦下了这件事,并说到:不是凭自己的本事,一个也莫想出来。
1985年,曾三疾病缠身,中央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喊一个能读得报的重孙去护理他。但去之前,又专门给益阳地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丑话讲在前面,我死后他是要回去种田的。那个孙子服侍了他整整6年,死了就真的打发他回来了!
虽然对自己的族亲曾三从来不松一丝口,但他对家乡的热爱确实最无私的,他回家乡探望时,问及村里老少的情况怎么样,当得知大家生活都很艰难时,立马把自己存了多年的工资捐给了村了,后来村里用这笔钱建了一个桔园,大大提高了村民们的收入。
曾三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到:“课堂、密室、牢房、草地、牛棚、会场,何谓人生幸福,酸甜苦辣都尝,生于伟大时代,分担天下兴亡,七五蹉跎有愧,应争晚节无伤。”这句话是他当着众多儿女的面说的,其中“生于伟大时代,分担天下兴亡”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自己一生都在为之实践的一句话,而这也成为了他留给后人的一条家训。

(曾三和家人合影)
1990年11月28日曾三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85岁。2015年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他是获奖章人之一。
